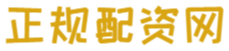股票杠杆平台开户
你的位置:股票杠杆平台开户_股票如何加杠杆_证券怎么加杠杆 > 股票杠杆平台开户 > 按月股票配资 对话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考古学让荒漠变成花园|“杰”出访谈_遗址_寺院_中国
这几年来按月股票配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多了很多回到家乡新疆的机会。
在吐鲁番火焰山南麓的一个小山岗上,他带领团队多次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开展科学发掘。
上一次对这个遗址的发掘,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当年进入吐鲁番的德国人,在考察报告中,记载了吐鲁番一个名叫西旁的景教遗址,并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景教文献。
后来,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批出土文献时,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流传到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景教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其历史与遗存见证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之一,是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国宝级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称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首。
展开剩余94%自2021年以来,由中山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发掘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以及新疆及中亚地区一系列的景教遗存考古发现,正在不断更新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近旁还保存有一些佛教寺院遗址,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存着。而在出土文献中,有些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这个现象揭示出当时多元文化共存情形,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刘文锁说。
关注西域地区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山大学重要的学术传统。去年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成果不断在各类校庆报道中被提及。
2025年1月,该考古项目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而在2023年,发掘获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中山大学马丁堂,与刘文锁展开了一场关于考古学人的对话。
1、中国最早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地
羊城晚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景教?
刘文锁:景教是唐代对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的称呼。过去认为它是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现在有些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的景教属于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或东方叙利亚教会。不过我觉得还是用景教这个称呼比较合适。
景教在唐代初年传入中国,在唐代晚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比较低沉,到元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一些上层社会人士都接受了景教。从考古发现上看,景教在唐至元代的西域新疆地区一直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羊城晚报:在此次发掘前,我们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有什么了解?
刘文锁:从文献记录来看,这个遗址在清末的时候已经被当地人发现了,而且可能盗掘出了文书。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1905年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探察时,从当地人那里获知了发现文书的信息,他们就按照这个线索找到了遗址。
据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记录,他们这次发掘出土了1000余件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献,主要是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其中也有一些世俗文献。由于东方基督教的文献比较少见,所以这一批出土物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该遗址中掘获有七件叙利亚语哲学残篇,因过于残破,长时间未能比定具体内容。中国学者林丽娟博士近来重新缀合了这些残篇,将它们正式比定为叙利亚语版亚里士多德所著《范畴篇》(Categories)第十章的部分内容,这个成果已经发表。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流传到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更新了中亚和中国亚里士多德著作流传历史的认知。目前,这些残篇保存于柏林。由于还没有系统整理,我们还不知道新获得的文书中是否也有他的著作残篇。
这个遗址在1905年被德国人发掘之后,长时间没有被关注,只是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作了记录。截至2021年我们第一次发掘前,一个多世纪没有做过科学的发掘。
羊城晚报:您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时间,主持这个项目的契机是什么?
刘文锁:2018年中山大学与新疆大学共同建设“新疆历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按照科研计划,要深入发掘一些有显示度的古遗址,服务新疆旅游业发展,助推“旅游兴疆”战略。
中山大学向来有西域研究的传统,几代前辈学者对西域地区非常关注,投注了很多热情,所以当时我们想延续这个学术传统,最后选择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发掘。
也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在正式发掘之前,我们就计划把寺院遗址完整地揭露出来,呈现寺院的全貌,然后想办法进行保护和展示利用。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发掘而发掘,而是要考虑将来这个遗址怎样保护、展示。
羊城晚报:经过几年的持续发掘,我们对这个遗址有怎样的基本认识?
刘文锁:西旁景教寺遗址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北边,在火焰山南麓的一个小山岗上,遗址面积超过了25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从山坡一直建到山岗顶上。像这种山丘型基督教寺院,在地中海地区是比较常见的。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明确了寺院的形制布局,以及当时上下山出入寺院的路径、葡萄种植地、墓地等,寺院的面貌越来越全面。总的来讲,它是一所比较典型的中亚、西亚地区那种建在山岗上的修道院,保存得比较完整。
2、不同民族和平共存的可贵启示
羊城晚报:有哪些代表性发掘成果?
刘文锁:我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寺院遗址本身,它的建筑保存得比较好,结构完整,这在全世界都是比较罕见的。
二是遗址出土了大批文物和自然物。这些文物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文献了。过去德国人挖掘出了有 1000件左右的文献,经过三年的发掘,我们发掘出的文献数量已经超过了1280件(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单论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这是国内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
从文物角度看,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的情况,以及壁画残块在颜料、绘画技法等方面与本地佛教等壁画相似的现象,揭示出当时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鉴的情形。
除了文献之外,遗址还出土了一批包括壁画在内的各种遗物以及动植物等样本,其中有像瓷器、钱币、漆器等来自中原的一些器物。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自然物的样本,植物样本是最丰富的,像各种蔬菜、瓜果,干化以后都保存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吐鲁番这个“天然博物馆”的优越条件。有机质遗物和样本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保存下来的。
此外,遗址出土的产自中原的北宋漆碗和“熙宁元宝”钱币,以及玉雕十字架、木斗拱等,则是当时景教中国化的鲜活证物。
羊城晚报:通过这些发现可以还原古代修士怎样的生活场景?
刘文锁:从我们测定的年代来看,这个寺院的存续时间为唐代到元早期,延续了几百年时间,最后遗留下来的废墟被我们发现了。
这个遗址可以还原出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上一个景教寺院是如何存在的,也就是景教在东传过程当中,它在古代西域地区如何生存,尤其是如何跟吐鲁番本地其他的宗教共存。
从出土的景教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在这里和平共存。比方说景教的经典都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但是也有大批用回鹘文书写的景教文献,这显然是面向当时生活在吐鲁番的回鹘族信众。不同的民族信仰景教,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和平共存,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可贵的启示。
羊城晚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蔬菜,可以由此推断当时的食谱吗?
刘文锁:这是可以的。三次发掘中都很少见到动物骨骼,这个情况验证了我们的推测,就是当年修士的生活是很清贫的,他们追求清修。他们应该是素食者,或者以素食为主。可是在前两次的发掘中没有发现蔬菜,出土的都是一些粮食作物和瓜果。
碰巧的是,在2024年发掘寺院北坡的居住生活区时,我们在山崖上发现一座洞窟。它最早可能是居住或者有别的用处,后来这座洞窟可能有些塌陷,修士们就把它当成了垃圾坑。我们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厨余垃圾,主要是大量的蔬菜。这样一来,就可以还原那些僧人当年吃的都是什么蔬菜。
另外,我们在垃圾坑旁边一间寝室的门口还发现一座非常精细的烤炉,就像维吾尔族烤馕的馕坑一样,很袖珍。我们也因此推测,当年的修士们很有可能是把烤饼当作主食。
羊城晚报:您前面提到,在遗址周围也发现了葡萄种植地。能够反映怎样的历史情况?
刘文锁:其实2021年我们已经发现了葡萄酒窖,在山顶区西侧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排列整齐的大陶器,经取样检测发现了葡萄籽的残留物,所以可以肯定那是一座葡萄酒窖。
基督教的弥撒等仪式中离不开葡萄酒,它在基督教中有特别的含义。在做弥撒的过程中,基督徒要领圣饼、饮葡萄酒。我们发现了酒窖、酒杯,甚至还发现了几块面饼,那么酿酒的葡萄是怎么获得的呢?它是修士自己种的,还是通过交换得来的?我们非常好奇。
结果在去年,我们在山岗东坡清理垃圾堆的时候,发现了种植葡萄的梯田,这可以证明,在寺院的早期山岗东坡曾经被开辟成梯田,用来种植葡萄。今年我们想扩大清理这个区域,弄清楚葡萄地的范围。另外,还想找一找它的水源是怎么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答寺院葡萄供应的问题。
3、系列考古成果形成国际学术新热点
羊城晚报: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从唐代一直存续到元代,这个寺院最后没落或者被弃用的原因是什么?
刘文锁:现在还找不到明显的证据。元朝历史上发生过一个很重要事件,元史上把它叫作“西北宗王之乱”,忽必烈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平定藩王叛乱。当时吐鲁番这个地方受到了波及,有人认为高昌故城就是叛乱期间被毁坏掉的。
我个人看来,像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很可能也是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战乱会导致人口的逃亡,很多城市因此消失,我想西旁景教寺院的衰落很可能跟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
羊城晚报:新疆考古成果丰硕,受关注度高。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在众多成果中占据什么位置?
刘文锁:景教有关的遗址,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也不多见。因此从考古学来讲,它可以填补很多景教考古的空白。
过去做景教史的研究,首先会利用明代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来就是靠一些文献来做研究。现在这个遗址发现以后,可以提供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新发现的大批景教文献和壁画。我想这个遗址的发掘首先是推动了景教考古,再进一步推动了景教史的研究。
那么我们再放大一点,景教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它与古代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共存、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世界基督教史等的研究都是相关的,所以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就新疆本地而言,除佛教外,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遗存保存下来的也不多。像摩尼教寺院遗址到现在都没有科学发掘过。
羊城晚报: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发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刘文锁:自2021年发掘以来,项目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我们在《西域研究》发表过本项目的阶段情况报告,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作了介绍,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这鞭策着我们要努力把项目工作做好,及时把考古成果公布出来,与学术界同仁分享。
在《考古学报》《考古》期刊的有力支持下,2024年8月,我们的前两次发掘报告和简报发表了。2024年10月,我们在吐鲁番召集了“景教研究新进展:考古,历史,文献,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又组织了数十位与会的中外学者,实地考察了这个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一些著名专家对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近年来,有多处景教遗址被发现、发掘。比如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奇台县唐朝墩古城发现并发掘的一座景教寺院遗址,寺院建筑结构保存良好,还出土了大量的精细壁画,其发现的惊喜度和重要性,与我们的西旁遗址隔着天山一南一北相呼应。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也不断有景教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一系列的考古成果推动着国际景教研究,甚至形成了景教研究的热点。
羊城晚报:当前,考古学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它研究的很多问题又被认为是“冷门绝学”,比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文献解读。在您看来,考古是“冷”还是“热”?
刘文锁:这个学科研究的很多问题,确实有点“冷”,包括这个学科本身。大部分人一联想到考古学,就觉得很辛苦,好像一说我是干考古的,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其实辛苦不辛苦完全是个人的体验。
毫无疑问,考古学这些年正在走向大众,考古学不是象牙塔,而且考古学尤其不应该是象牙塔。因为考古学的对象是文化遗产,这个遗产是全人类的,考古学应该有一种开放性。
包括像我们的考古工地,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我觉得应该越来越开放,甚至采用志愿者制度来发掘,让公众随时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只有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考古工作,才能获得他们更多的支持。所以考古学应该是越来越开放,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现在正在这样。
羊城晚报:这其实也能消除误解,比如很多人提到考古就联想到小说《盗墓笔记》。
刘文锁:是的。《盗墓笔记》是文学作品,真实的考古学并不是这样的。在考古遗址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好能向媒体开放,向公众开放,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考古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考古发掘过程本身还是蛮枯燥的,确实很累。很多文学作品关于考古工作的想象都是浪漫的。当然,考古学需要浪漫化,否则这个学科可能很多人坚持不下去。但是考古学的浪漫化不仅仅体现在发现宝藏,它本身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在里面。
4、田野学科永远不会枯竭
羊城晚报:您在新疆出生长大,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广东?
刘文锁:我就是冲着中大历史系来的。我是中大历史系第一批博士后,合作导师是历史系林悟殊先生。我还记得当时在永芳堂的宗教文化研究所办公室,林悟殊先生和时任人文学院院长的陈春声教授对我的面试。
当时有一位同届同学,知道我要到中大,送了我一本《追忆陈寅恪》,让我多了解中大学术的传统和精神。后来跟着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林悟殊先生这些前辈学习,不断在他们身上感悟到从读书治学到待人接物上的返璞归真。
无论是治学传统还是地域精神,广东的精神就是务实。在广东生活的这些年,使我越来越认同自己也是广东人。
羊城晚报:考古也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对您而言,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文锁:专业上的事情再难都不是难事,我倒是觉得当考古领队是非常难的,什么都要负责。每次下田野我的压力都好大,有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人际关系是我的弱项。
羊城晚报:您今年刚好60岁,对于很多学者而言,似乎没有退休的说法,您之后有什么计划?
刘文锁:学校批准我65岁退休,我到了那个年龄该退就退,这没有什么。退不退休都各有生活法度,等退休了我还有好多事情想做。我觉得只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就很好,没有说著书立说就是更好的,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羊城晚报:您觉得以后会怀念田野考古的经历和时光吗?
刘文锁:在我的一些前辈里,80岁还在下田野。
像今年2月份刚刚去世的王炳华先生,他是新疆考古学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2014年时他80岁,我们还一起去了尼雅遗址,沙漠里面晚上零下20多摄氏度,他照样跟我们一起扛过来了。
总之考古学界的老先生还是挺活跃的。将来退休以后,如果有年轻人愿意邀请我去工地看看,我也很乐意去的。
羊城晚报:考古经历真的塑造人的一生,比如性格和体魄的锻炼。
刘文锁:是的,考古学说的田野有它的魅力,就是从实际中获取知识。它总是突破那些有限的东西,能够获得的好像永远不会枯竭。
过去有人说,考古学是探险英雄的学科。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里就把考古学家塑造为一个探险家,这是艺术化的表达。而考古学者就要有探险精神、探险技能。探险不是冒险,而是意味着探索未知的世界。保持求知欲是学考古的基本素养,缺乏求知欲,学不来这个学科,也做不出成就。
我也期待学生能够有考古学家范儿,学识渊博、专业熟练,也能在野外处理很多实际问题,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文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文艺 梁善茵
图 | 受访者提供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策划:陈桥生
统筹:邓琼 侯恕望 吴小攀
主持:朱绍杰
执行:周欣怡 文艺 梁善茵 何文涛按月股票配资
发布于:广东省- 2025-01-03股票配资是做什么的 破折号的使用技巧与输入方法详解
- 2025-03-18股票配资赚钱 壹网壹创: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2025-01-07股票融资利息怎么算 告诉你一个,不困的秘诀! | 漫画
- 2025-03-25期货策略平台 外媒:《寂静岭f》或引领《生化危机9》变革
- 2025-01-03融资杠杆怎么用 REDMI新款平板或采用8.8英寸小屏,搭载天玑9400满血旗舰版?